-

联辉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软件,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需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单位面临的:基建财务核算和业务管理日益繁杂、不同层面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披露具有不同的需求等问题而开发的专案产品。
-

联辉公司的小快记所具有的快速建账、凭证管理、账册输出、报表管理等功能可将财务人员从大量而繁琐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效降低差错率,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使财务人员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账务管理上,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财务业务的长处,且无需花费过多的精力在学习软件上,即可轻松做账,放心交差。
-

联辉小快记[专业版]是联辉公司针对广大从事代理记账的会计人员、代理记账公司以及小企业量身订做的一款软件产品。此软件可管理99套账。各长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其中复制套账功能,可节省您的建账时间,取其有用,去其无用。轻松进入工作状态。
-

联辉【随身宝】财务软件,是一款专门为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兼职会计而设计的移动财务软件。是面向他们的财务工具,它以U盘为载体,免安装即插即用,可实现财务数据的随身携带,由于其独有的特点,完全可以帮助中小企业会计人员做到轻松记账、财务随行。
【故事梗概】
《春月》中的主人公都是中国人。故事从光绪五年写到1972年,以“春月”这个出生在封建专制家庭的女人为主线,描写了两个老式家庭五代人的经历。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漫长岁月的动荡和变迁,堪称为一幅历史画卷。
故事结束时,春月已经是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显示了自己既通晓中国近代历史,熟悉中国风俗习惯,又能熟练地遣字用句,安排情节,塑造人物的才华。
主要人物表
苏州张府
英才 老太爷及其正房夫人老太太的长子,族长
栋才 老太爷及二姨太的儿子
玮才 老太爷及三姨太的儿子,军人,国民党
香雪 栋才的妻子,春月的母亲
春月 栋才的女儿
金贞 英才的妻子
桂风 远亲,资本家
小刚 佃户老李的儿子,革命者,共产党
胖妈 张家忠诚的女仆。
北京吴府
威正 翰林
莲怡 威正的妻子
庆程 他们的儿子,变法者
莹琨 庆程的女儿,革命者,共产党
永程 威正的养子
哑巴 女仆
作者简介
贝特.包.洛德(包柏漪)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四六年随其作为国民政府官员的父亲赴美公干来美。其妹时年尚幼,留居国内,寄养在亲属家。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包家遂定居美国。一九六二年,其妹离开中国。其妹在国内的生活和与家人团聚的始末是洛德夫人第一部作品《八月》的主题。
一九七三年,洛德夫人随其夫温斯顿.洛德重返祖国。她与亲属的重聚构成了《春月》的素材。
洛德夫人毕业于塔夫茨大学,并获得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硕士学位。她现在与丈夫及女丽莎、子小温斯顿住在纽约。其夫温斯顿.洛德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新 嫁 娘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诗经》
张府的庭院锣鼓喧天,喇叭、铙钹、笛子和鼓的合奏四处回荡。春月开始登上北京之行的十天旅程。她头上戴着缀满宝石的头盖,脸上挂着面纱,红花轿的门窗用帘子遮住。妇女们说,新娘子的官人不掀她的面纱,她是不许任何人看的。
去上海的油篓船舱里要挂帘子,驶往北方的轮船舱房里要挂帘子,由天津开往京师的火车软席车厢里也要挂帘子。春月每换乘一种交通工具,都要先戴好头盖,掩好花轿的门窗。一路上,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城市的喧嚣、潺潺的流水声、隆隆的车轮声、巨人心脏跳动般的火车发动声。
春月最初让胖嫂和老鹰头在门外站岗,好让她偷看看外面的风光。如果他们不答应,她也只好听从,无精打采起来。
她对即将来临的事想的不多,总想她的老家。送亲宴会总算过去了。祖母因为牙掉光了,所以笑口不常开,母亲则话不绝口,大谈未来的外孙子。这边父亲也填了两阕词,一阕赠庆程,一阕给她。两阕词准备挂在她的新居。“春月已去,对伊去不甚知闻…….”这是送给她那一阕的开头。在她记忆中,这是父亲头一次关心她的表示。三叔来信表示歉意,并赠一尊唐三彩马。她想,他送这匹马并不是因为它精致美观,而是作为他枕戈待旦的标志。这不算什么。她一定珍惜它,因为这是三叔的心意。
只是大伯脸上毫无笑意。她不理解,在她大喜的日子里,到底什么事得罪了他。
火车驶抵北京站,她最后一次裹上了绫罗绸缎,脸上盖好红面纱,再蒙上缀满宝石的头盖,被关在轿子里。花轿摇摇摆摆向前走,走过陌生的无休无尽的大街小巷,最后,花轿总算停了下来,锣鼓声穿透了令人窒息的黑暗。她到了她婆家的院里。
她渴望把轿门打开,她让她自由地透口气,看看外面,哪怕白日的阳光透过面纱,透进些红光也好。不过按照礼俗,还要耐心等待三支曲子演奏完毕,从而证明新媳妇温良恭顺,这才能打开轿门。她宁可憋死,也不能落个急不可待的话柄。
音乐总算奏完了。短暂的寂静。然后是渴望已久的三次敲打声,接着又是撕纸的声音。一缕清风撩开一角面纱。空气里弥漫着炷香的气味。
她知道四周围满了人,他们鼓掌欢呼,“新娘子!新娘子!”她真想偷瞧他们一眼,可是她看见的只是新娘红绣花裙上的龙凤和小小的红鞋尖。几双温柔的女性的手轻轻搀扶她下轿,帮她站稳。两条坐麻了的腿还能不能撑得住她,一时真没有把握。如果她东摇西晃,如果哪怕有人在刹那间想到,张府送来的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姐,那也真够丢脸!那几双手一直扶着她,直到她站稳为止。然后她在这些陌生女人的搀扶下一步步向前走,这些女人不久就是她的姐妹和堂表姐妹了。
路上铺着红毡。礼堂里是木地板,板与板之间缝很深。她一迈过门槛,看见她面前几尺远的地方是一双男人的白色千层底的布鞋和蓝绸长衫的下摆。
一个瓮声瓮气的嗓音宣布拜堂开始,乐队开始吹打。这铙钹声和鼓声,莫非是自己的心跳声么?她看不见,又不能说话,只能由别人领来领去,一次又一次地下跪,叩头,受礼的人都是她自己家的人或是亲友。
她不明白,甚至感到迷惘,他们怎么就知道她是真正的新娘,而不是被别人胡乱穿戴好硬塞进花轿里的别家姑娘呢?也许是她自己弄错了吧。也许是她到了另一个世界。奇怪的是,这种想法并不使她苦恼。她觉得自己正在做梦,仿佛她曾经附在别人身体上体验过这种生活。先老太爷对她说过什么来着?……要听话呀,孩子,要听话。
喜乐戛然而止,人群中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她如今已经是同她并肩走、同她一起叩头的那个男人的妻子了。爆竹声和乐曲声响成一片。
热闹的场面还在持续。喜娘们却把她从礼堂里领出来,沿着花园的小路,迈过一道道陌生的庭院的台阶。她眼前能看到的。总是她丈夫那件蓝绸衫的下摆和白色千层底布鞋。最后,他们走进房间,她被指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屋里是乱哄哄的一片温和的笑声、低语声、碟子的磕碰声和金莲进进出出的走步声。不一会儿,门关上了,屋里静下来。
她等着,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走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她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冷静,聆听着。她忽然觉得头盖太沉了。她伸手摸摸脖子。
这时有人清了清喉咙,吓了她一跳。原来庆程一直呆在屋里。她低下头,闭上眼睛,倒要看看他什么时候开口。她不能先开口。他走过来,坐在她身旁的长靠椅上,仍旧一声不吭。她一时觉得头有些晕。现在可不是头晕的时候,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她祈求着。她万万不可晕倒,也不能碰男人的衣服。他冷不防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来踱来踱去,喃喃自语。
他说的话没有什么含义。她听得出,英才每回用英语自言自语时,就是这种调子。她心里立刻感到轻松了。
他刚才起步是那么突然,现在停步也干脆利落,又坐到她身边来。两个人又相互等待。过了好久,他大声说,“小姐,我的朋友英才好吗?”
现在她可以开口了。“原来你不是又聋又哑呀。”
“你想到哪儿去了,”他的语调使她满心欢喜。
“谁让你一句话也不说呢。”
“你也没说话呀,”他的反应很快。
“可是我以为不该由我先开口。”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是这么嘱咐过我的。”
“他们没对你说过我的身体没毛病吗?”
“没有,”她骗他说,“我没问过。”
“你没有问过?”
“是的,什么问题都没问过。我不知道你是驼背,还是大个子,是花花公子,还是一头大公牛。”
“这么说,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嫁喽?”
“那当然啦!”她这么说,他会不会以为她没受过教育呢?“婚姻大事要听父母的。”她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她听到他叹了一口气。“我也是这样,”他终于说了。“我 对你也是一点不了解。”
“一点不了解吗?”难道他也在撒谎?
“一点也不了解,和你一样。我把婚姻大事完全交给父母作主。”
“那就是说,任何女人你都可以娶喽?”
“正是。”
“唉。”她失望了,腰板挺得更直了。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庆程站起身,把桌子拉近。她闻到北京烤鸭的香味。
“我们吃点东西吧。客人们一会儿就来,可能要呆一宿。我们现在要是不吃,就没有机会吃了。”
“我可不能蒙着这个吃。”
“摘掉好了。”
“那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非得你摘不可。”
“我猜这也是他们教给你的。”
她点点头。
“那好,那就请你先站起来。”
“劳你驾,大哥哥,请扶我从桌子后面出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庆程走到桌子另一端,把桌子从她身前拉开。“现在就站得住了。”
春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低垂。他小心翼翼地摘下缀满宝石的头盖,然后又掀开面纱,都放在桌边上。耀眼的光照着她,她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她慢慢把眼睛睁开,抬起头来。她眼前正是一粒金钮扣。她再慢慢往上看,又是两粒金钮扣,然后才看见丈夫的脸。丈夫很高,皮肤光滑滋润。她抬头看他的面孔时,他满面笑容。
春月羞红了脸,立即坐了下来。“我们的饭菜都快凉了。”
她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他开始说了点什么,后来便不说了。她举起筷子去夹对虾,蓦地又记起要注意举止,连忙又把筷子放回原位。她偷看他的表情。他俩的目光碰在一起了。他显得有些慌乱,茫无所措地转动着右手中指上的戒指。她则只管望着菜肴,馋涎欲滴。终于,他走到桌子另一端,坐下来。饭菜真香啊!
两个人谁也不动手。难道他老是这么看着不成?他要是不想吃,她可就不客气了!两个人同时举起筷子,都想夹同一个鹌鹑蛋。
“请,你吃,”她说。
“不,你请。你是客人。”
“我是客人?”她迟疑半晌。“好吧,你要不吃,我就吃。”
她吃得津津有味。他默默地拣拣吃吃,把菜放在他从未碰过的碟子里。他看着她吃了四张卷烤鸭的荷叶饼、五只对虾、两个饺子、两枚长寿蛋、三块酱牛肉、六个瓤馅蘑菇和一整份樱桃肉。
“你是胃口总是这样好吗?”他问。
“你的胃口总是这样坏吗?”
庆程脸红了。
外面敲门,喜娘进来收拾餐桌,其中一个跑出门去大呼:“美人儿!真是美人!”新娘新郎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一个年纪最大的女仆做手势让新郎出去。
喜娘们再一次给春月涂上口红,把一绺松下来的头发卷上去绾住。这时,她环顾四周,头一次观看她的房间。难道真比慧心院的会客室小这么多?还是因为屋里家具太多的缘故?也许等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婆婆会答应变动一下的。
女仆们离去了,其中最俊俏的一个故意呆在门口,向庆程示意。“好福气的新郎官,”她说话的声调就象唱歌。“您现在坐在新娘子旁边吧。家里人和亲威朋友就要来闹新房了。”
庆程顺从地走了过去,嘟哝着说,“又一条陈规陋习。”
春月悄声问道,“很可怕吗?”
“但愿不太可怕。依我的意思,开过玩笑就算了。他们让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要不然他们使起兴来,一呆就是三天三夜。”
最先进来的是新郎的父母。虽然莲怡和威正的衣着都很考究,但在春月看来,女服显得时髦,男服却象是借来的。莲怡的身材相当高,也有些姿色,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威正胖乎乎,蓄着淡黄色胡须,脸上有麻子,但很慈祥。
莲怡先说话,“好,好,好,我倒没料到新娘子生得这么秀气。你说呢,老爷?”
“是,当然,没想到。儿啊,你福气真好,你父亲虽丑,却也有俊秀的朋友。”这回答使春月愕然。胖嫂告诉过她,大伯早就把他给春月在挚友塘畔柳树下拍的一张照片寄给这位翰林了。看来,她公公并没有把那张照片拿给婆婆看。
婆婆嘴角上略带一丝笑意,不过声音是冷冰冰的,“那我们就看看你那位俊秀朋友的孙女懂不懂孝道了。”
春月暗忖,也许等生了第二个儿子再要求调换家具,这样更明智些。
公婆走后,吴家的女眷们把她团团围住。她一时只觉得自己是一只退了毛的小鸭,人家要拿她下锅当盘中餐了。
“哎唷,哎唷,这些头发都是你自己的吗?”
“让我们瞧瞧你的金莲。”
“有点瘦啊,你们说呢?”
“啊,照我看,还显得肥呢。”
“你们说她是不是滑头,南方人不都是滑头吗?”
“说不定是绣花枕头。表面好看,里边什么也没有。要说她连喝酒都得掂量好几遍才决定用杯子的哪一边喝,我听了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随她们说去。她是张家人!
女人们正你一刀我一枪收拾她时,男人们站在一旁盯着她,真心诚意向庆程道喜。
年长的宾客逗留时间不久。他们一走,就换来一批未婚青年,挤满了一屋,又嚷又叫。有几个搬来八仙桌和椅子,立刻坐下来打麻将,其他人便遵照俗例,你一言我一语地质问、挖苦、模仿和捉弄这对新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想出各种鬼花招,使春月不能自持,设法使她笑,使她哭,使她发火。然而实际上,春月却表里一致,心里冷静得很。这些人的手段远不如胖嫂那些手段。
其中一个讲了个淫秽的故事,气得庆程咬牙切齿,但是春月悄悄叮嘱他,“记住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们不能让他们呆三天三夜。”
不出一个小时,连最无聊的一个家伙都泄了气。他一走,全都散了。
不一会儿,喜娘们又回来铺床。床设在耳房,挂着红床帐。庆程再一次去花园里等候,春月仍端坐不动,暗自微笑,她很喜欢他。
喜娘出去后,胖嫂进来打开陪嫁的皮箱,帮助新娘换去结婚礼服。春月抓住了这个时机。“快!快!你说说你听见底下人说了些什么。”
胖嫂正从衣箱走向衣柜,听见她问,便走了过来。“您婆婆脾气可不好。要多加小心,讨她欢喜。”
春月不耐烦地摇摇头。“不,不。关于他,你听见了些什么。”
“翰林倒是个好人,可特别怕老婆。”
“不对,不对。你这个傻瓜真急死人。不是他!我指的是我的男人。”
“啊!”胖嫂支吾起来。“您亲自见过他了,再说,和他有什么相干?”
她转过身,把梳妆用具放在梳妆台上,春月抓住她的袖子。“你听说了,一定要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
“没什么。不是现在的事,您现在已经结婚了。”
“如果别人都知道了,我倒不知道,我怎么能当他的好媳妇呢?”
胖嫂让她说动了。“底下人说,少爷当初不想结婚。”
“她们说为什么了吗?”
“这不关您的事,我的小乖乖。她们说他学洋派,不喜欢父母包办的婚姻。他要娶的是他见过的、合他意的、他自己看中的。”
“这样的人是谁呢?”
“没有。没有那么个人。所以翰林才拿主意了。快点吧,该换衣服了。”
春月不再多说,脱下一件又一件红绸红缎的衣服,换上绯红色长睡衣,隐约衬出她苗条的身材。胖嫂刚才的话,她越想越放心。大伯绝不会让她嫁给一个不爱她的男人的。
当胖嫂对里里外外都觉得满意之后,便热情地把姑娘搂在怀里,悄悄嘱咐她说,“别忘记我教给你的那件事。别忘记那块白绫子。”春月羞红了脸。阿弥陀佛!她由衷感谢老仆人对她的开导。胖嫂要是不说,她准会被母亲那套这棵树那棵树的理论弄得不知所措。
新娘子又独自在卧室中间站了一会儿。
在她面前的是雕花的黄檀木床,上面是绣得精细的帐顶和红帐幔。红缎床单上撒了许多玫瑰花瓣和五颜六色的婴儿鞋。床边有个小茶几,上面盘子里就是那一方白绫。第二天早晨,她必须把这块白绫交上去,证明自己的贞操和改做吴家人的真心诚意。
她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看,庆程正站在门口。她看到他正在打量屋里的一切,望着床上作为子孙满堂的那些标志,望着盘子里盛的那方白绫,最后才注意到她正站在那里。她看不见他的脸。
他站了老半天,一动不动。忽然,他毅然走到茶几前,一脚把茶几踢开。他拿起那块白绫,使劲扔出去。白绫在空中飘飘忽忽,又落到他的脚下。他气忿已极,一扔再扔,他扔不远,已经气喘吁吁了。
开始她还以为是他厌恶她。后来她明白了,不是这个原因。他的举动真象个孩子。胖嫂没有说错。他不愿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结婚。
无论是她母亲还是胖嫂,事先都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一情况。两个人一直沉默着,唯一打破沉默的,是他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她知道她该怎么办。她也象他那么果断,走到床边,抄起一双红婴儿鞋,使劲往远处扔,扔了一双又一双。
后来,谁也不记得是谁先笑的。两个笑个不停,直笑得弯下了腰。最后,他问,“为什么你这么做?”
“为什么你这么做?”
“是我先问的你。”
“我认为你不喜欢那些旧礼俗。”
“你呢,小妹妹。”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接着说,“你说得对。我恨旧礼俗……不愿意娶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她忙伸出一只手,象是去堵他的嘴巴。“大哥哥,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不能不承认双方家庭已经做了的事。可是我们不会永远是陌生的人。萍水相逢的人也会互相了解。”
“那需要时间。”
“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大哥哥。”
“你不会等得不耐烦吧?”
她羞红了脸,摇摇头。初次见面就有这么多事。她能够等下去的,让她高兴的是,她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情,她知道她能使他露出笑容。
“小妹妹,你当真理解吗?”
她寻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比她的还要圆,那是一双北方人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谁的都不同,这是她丈夫的眼睛。她记得他问过她的话和他的喁喁私语,“是这样的。”两个人好半天没有说话,谁也不动一动,象是连呼吸都停止了。他们休息够了,她开始在扔满一地的婴儿鞋中找东西,爬来爬去,顺手把小鞋东抛一只西抛一只。
“你在干什么?”
她把食指放在嘴唇前。“嘘!”
她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那块白绫。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她就一口咬破嘴里腮边的肉,把鲜血啐到白绫子上,血迹斑斑。
她做完后,不顾疼痛,含着微笑把白绫递给他。“这是我们俩头一个秘密,我的丈夫。”
他们收拾好屋子,恢复了新房的原貌,这时天已放亮。新郎新娘谁也不承认疲倦。庆程提议提前吃早饭,她同意。他走出去叫仆人,仆人立刻就把早餐端了进来。
桌上摆好,仆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又坐了下来。她吃得很小心,注意用嘴的右边咀嚼。
“这些面食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她说着又拿了一块。
“你会烧饭吗?”
她摇摇头,沮丧地叹了口气。接着便是沉默。后来她问,“如果鱼烧不成整条的,婆婆会怪罪我吗?”
“你说些什么呀?”
“他们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
“起初我们俩悄悄地过三天三夜。第四天一早,我就必须打扫,并且给全家烧一条鲤鱼。”
“为什么呢?”
她两颊飞红。她怎么好说,这是婆家试新媳妇手艺,而且也是盼望多子多孙的象征呢?她摇摇头。“习俗真不少。”她皱起眉头,把筷子放下。“要是烧得很糟糕,你能多吃点吗?”
“到底为什么呢?”
“噢,请你一定答应我。我要对婆婆说,这是我们苏州的特殊风味,不是人人头一次尝就会爱吃的。你假装说你爱吃,可以吗?吃完再要,接着又要。除你以外,谁也不愿意吃。”她做了个鬼脸。
“你要我骗我母亲吗?”
“啊,不是!你什么也不要说,只管吃就是了!”她笑了。“可以吗?”
他点点头,象是在窃笑。“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秘密。”
他们都笑了,但是她躲着他的视线。
她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这也真不错,确实怪惬意的。她又接着吃下去。他只举着筷子,看着她吃。
“小妹妹,你一定绣得一手好花。”
“我绣花笨得象一头熊。”
“我想你一定是过分谦虚了。”
“不。”春月又叹息了。“不,这是真话。我不喜欢刺绣。”
“那么你一定会画扇面—-画花,画隐在云雾里的山,对吗?”
“我也不喜欢绘画。”
“那么你一定喜欢种花。”
“不。”她喝了一口豆浆。
“要不然,会唱歌,或者会弹琵琶?”
她放下碗,低下头。“我一无所长。”
他望着。
她想,噢,我这是怎么了?他一定拿我当饭桶了!于是她突然问,“你呢?”
“我什么了?”
“烧饭,刺绣,绘画,园艺,唱歌或者弹琴?”
“全不会。”
“太妙啦!”她拍起手来。“我们共同之处可真不少。”
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沉默。
“我去叫人拿一副牌来,好吗?”
“不,我不打麻将。”
“噢,”他说。露出困惑不解的样子。
“你会下棋吗?”春月坦率地抬头望着他,遇到他的目光。
“我?当然会。”
“啊!”她拍拍自己的太阳穴。“下棋是动脑筋的游戏。”
“很不容易。”
“你这里有棋吗?”
“有。”
“好,我们摆上棋盘吧。”
“你会下棋?”
“稍会一点。”
他叫仆人收拾饭桌,收拾完以后,他从书桌里取出一副老式象牙棋。她望着他把棋子摆好。她不声不响地先走了第一步。
她打退他的攻势,佯装没看见他抓耳挠腮的表情。最后,她用炮发起决定性的一击,他便不再看棋盘了,靠在椅背上,两手搭在胸前,开始研究起她来。她只管看着下面。他忽然又问,“你识字吗?”
“识几个字。”
“也跟你下棋一样——稍会一点?”
她本想不回答,两手捂着嘴,怕笑出来,然后点点头。
更夫打点,戌时到了。他们连连打呵欠,抬不起眼皮。可是谁也不想先提出去睡觉。他们各自在椅子上打瞌睡。亥时,更夫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两人无精打采,昏昏沉沉。他说,“我们不能天天睡在椅子上呀。顶好上床去睡,你说好不好?”
她点点头,然后,她的两眼盯着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问道,“我一个人先进去,可以吗?你什么时候进来,等我喊你。”
“随你的便。多久都行,小妹妹。”
“她走进卧室,换了衣服。她准备停当以后,又把被子卷成筒状,上了床,再把被筒放在中间当屏障。不一刻她便一动不动地躺好,然后撩起被单,喊到,“大哥哥,你可以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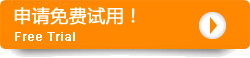

 史晓琳
史晓琳 汪小静
汪小静 曲建如
曲建如 宁新勇
宁新勇 刘冲
刘冲 傅波
傅波 张宏志
张宏志 张经理
张经理






